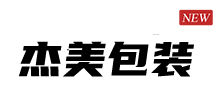深圳欺詐罪辯護(hù)律師 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刑法(十一)
近幾年,我國(guó)資本市場(chǎng)發(fā)展迅速,證券欺詐發(fā)行、虛假披露等犯罪案件不斷增加。2010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與中國(guó)證監(jiān)會(huì)聯(lián)合發(fā)布了《證券違法典型案件通報(bào)》,指出:“自十九大以來(lái),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共作出行政處罰決定810件,市場(chǎng)禁入決定82件,罰沒(méi)款總額達(dá)193.04億元。從2017年9月開(kāi)始,全國(guó)檢察機(jī)關(guān)共批準(zhǔn)逮捕、起訴各類(lèi)證券期貨犯罪302人,提起公訴342人。今年1-9月,批準(zhǔn)逮捕102人,起訴98人,同比分別增長(zhǎng)15%和27%。
增加違法成本是資本市場(chǎng)多年的共同呼聲,也是資本市場(chǎng)改革的重點(diǎn)工作之一。尤其在注冊(cè)制改革中,如何遏制和嚴(yán)懲欺詐發(fā)行、虛假披露等違法違規(guī)行為,是市場(chǎng)最為關(guān)注的問(wèn)題。所以,要重塑資本市場(chǎng)良好的發(fā)展生態(tài),就必須對(duì)欺詐發(fā)行、財(cái)務(wù)造假等惡性違法行為保持“零容忍”,重拳出擊,重拳出擊。[1]自從新證券法于2020年3月1日生效以來(lái),加快修訂刑法的呼聲就越來(lái)越高。
2010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第十三屆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第二十四次會(huì)議通過(guò)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對(duì)刑法中有關(guān)證券違法行為的條款進(jìn)行了修改,其中主要有四項(xiàng):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操縱證券交易價(jià)格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在此基礎(chǔ)上,選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個(gè)案例,分別是“欺詐發(fā)行股票、債券罪”和“違規(guī)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期對(duì)正確理解《刑法修正案(十一)》對(duì)兩個(gè)關(guān)鍵罪名的修改有所幫助。
《刑法修正案(十一)》對(duì)“股票、債券詐騙罪”的修改情況及亮點(diǎn)。

采取兜底性規(guī)定的做法,擴(kuò)大本罪的規(guī)制范圍;
原有刑法對(duì)本罪的調(diào)整范圍采取了窮盡列舉式的規(guī)定,這種立法模式已不能適應(yīng)新《證券法》的變化。為此,一方面《刑法典修正案(十一)》采取兜底性條款,在“招股說(shuō)明書(shū)、認(rèn)股書(shū)、公司債募集辦法”等列舉條款之后增加“等發(fā)行文件”條款。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則將“存托憑證或者國(guó)務(wù)院依法認(rèn)定的其他證券”納入本罪的調(diào)整范圍,使得本罪的規(guī)定更加靈活,與新《證券法》的銜接更加緊密。
對(duì)本罪自由刑和罰金刑的刑罰配置作了全面改進(jìn)。
在原刑法典中規(guī)定的“五年以下監(jiān)禁或者拘役”法定刑基礎(chǔ)上,增加了第一檔法定刑,即“數(shù)額特別巨大,后果特別嚴(yán)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到目前為止,本罪自由刑的上限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此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刪去了本罪第一款中的罰金刑的數(shù)額限制,將罰金刑改為不限罰金刑,第三款中明確規(guī)定了單位罰金刑的數(shù)額不得超過(guò)“非法集資資金數(shù)額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一倍”。
第三部分增加了控制股東和實(shí)際控制人作為犯罪主體的規(guī)定。
在本罪第二款中,《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控股股東和實(shí)際控制人作為本罪犯罪主體,第三款更明確了控股股東和實(shí)際控制人作為本罪犯罪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從而強(qiáng)化了在以控股股東和實(shí)際控制人為主的欺詐發(fā)行案件中對(duì)控股股東和實(shí)際控制人的刑事責(zé)任追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違反規(guī)定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修改情況及亮點(diǎn)。
第一,改進(jìn)了本罪自由刑和罰金刑的刑罰結(jié)構(gòu)。
刑法典修正案(十一)將本罪自由刑的刑期改為:原刑法典規(guī)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改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增加了第一檔刑期:“情節(jié)特別嚴(yán)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此,本罪自由刑的刑期最長(zhǎng)可達(dá)十年。在罰金刑方面,取消了原《刑法典》法條中“并處或單處二萬(wàn)元以上二十萬(wàn)元以下罰款”的罰金刑數(shù)額,改為無(wú)數(shù)額限制的罰金刑。
第二節(jié)增加了控制股東和實(shí)際控制人作為犯罪主體的規(guī)定。
修訂后的《刑法》規(guī)定,本罪的犯罪主體只限于“依法負(fù)有信息披露義務(wù)的公司、企業(yè)”,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前款規(guī)定的公司、企業(yè)的控股股東、實(shí)際控制人,是本罪的犯罪主體。應(yīng)當(dāng)指出,這里的控股股東和實(shí)際控制人包括自然人或單位。另外,控股股東、實(shí)際控制人“隱瞞有關(guān)情況,致使前款規(guī)定的情形發(fā)生”的行為,也應(yīng)列入本罪的處罰范圍。
㈢對(duì)第二款所列單位犯罪采用雙重懲罰原則。
刑法典(十一)增加了第三款,即:“前款所稱(chēng)的控股股東、實(shí)際控制人是單位的,對(duì)單位處以罰款,對(duì)其直接負(fù)責(zé)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zé)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該增加的規(guī)定,改變了原刑法典中單罰制的原則,即原刑法典中對(duì)單位作為控股股東、實(shí)際控制人的單位也應(yīng)適用單罰制的原則,即單位作為直接責(zé)任人的單位也應(yīng)適用雙罰制的原則,即單位作為直接責(zé)任人的單位也應(yīng)適用雙罰制的原則。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關(guān)于“以欺詐手段發(fā)行股票、公司債券罪”、“違反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規(guī)定。
刑法典修正案(十一)增加了罰金刑和自由刑的設(shè)置,大幅度增加了對(duì)這兩類(lèi)犯罪的刑事處罰力度,將有效遏制證券欺詐、違規(guī)披露等違法犯罪行為。與此同時(shí),《刑法修正案(十一)》完善了兩罪主體的規(guī)定,嚴(yán)密了刑事法網(wǎng),彌補(bǔ)了對(duì)兩罪的處罰范圍不足,體現(xiàn)了新《證券法》全面推行證券發(fā)行注冊(cè)制,加大了證券違法成本,強(qiáng)化了信息披露義務(wù),為進(jìn)一步防范和化解金融風(fēng)險(xiǎn),維護(hù)金融秩序提供了有力的刑法保障。

新《證券法》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實(shí)施,一方面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信息披露要求,將“信息披露”單獨(dú)列在專(zhuān)門(mén)章節(jié)中,擴(kuò)大信息披露主體范圍,細(xì)化和完善應(yīng)披露的“重大事件”范圍,強(qiáng)化董事、監(jiān)事、高級(jí)管理人員以及控制股東、實(shí)際控制人的信息披露義務(wù),完善違反信息披露義務(wù)的民事賠償制度,建立控股股東、實(shí)際控制人的民事責(zé)任過(guò)錯(cuò)推定制度,突出了信息披露義務(wù)的重要性。同時(shí),加大了對(duì)證券欺詐、違規(guī)披露等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如果是欺詐發(fā)行,則罰款金額由“非法募集資金數(shù)額的1%以上5%以下”提高到“非法募集資金數(shù)額的10%以上一倍以下”;如果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法,則罰款金額由“30萬(wàn)元以上50萬(wàn)元以下”提高到“100萬(wàn)元以上1000萬(wàn)元以下”。
深圳欺詐罪辯護(hù)律師 這次修訂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著重與新《證券法》銜接,彌補(bǔ)了在對(duì)證券市場(chǎng)違法行為處罰方面存在的不足,修改前的《刑法》規(guī)定了對(duì)“以欺詐手段發(fā)行股票、債券罪”的自由刑,最高可判處五年有期徒刑,最高可判處五年的罰金。修訂前刑法規(guī)定的“違反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自由刑的刑期最長(zhǎng)可達(dá)三年,罰金刑最高可達(dá)20萬(wàn)元。相反,成熟資本市場(chǎng)對(duì)欺詐等行為的懲罰往往非常嚴(yán)厲,例如美國(guó)《薩班斯法案》規(guī)定,故意實(shí)施證券欺詐的罪行可判處最高25年監(jiān)禁,而對(duì)個(gè)人和企業(yè)實(shí)施欺詐的罰金則分別高達(dá)500萬(wàn)美元和200萬(wàn)美元。顯然,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出臺(tái)之前,對(duì)證券欺詐、違規(guī)披露等違法行為適用的《刑法》規(guī)定的懲罰力度過(guò)小,不能達(dá)到罪刑相當(dāng)?shù)某潭龋@也是我國(guó)證券市場(chǎng)出現(xiàn)違法違規(guī)現(xiàn)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