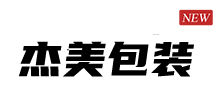(二)合同詐騙罪的本質(zhì)是被害人基于合同陷入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而交付財(cái)物
如前所述,在普通詐騙罪中也會(huì)存在以合同的名義實(shí)施詐騙的情形,這從表面上看與合同詐騙罪的犯罪構(gòu)成是相符的,使得司法機(jī)關(guān)在認(rèn)定時(shí)在普通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之間徘徊。因?yàn)槭欠翊嬖诤贤钦J(rèn)定普通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的重要區(qū)別,這就需要我們對(duì)利用合同進(jìn)行認(rèn)真解讀。所謂“利用合同”,是指通過合同的虛假簽訂、履行使得相對(duì)方陷入錯(cuò)誤認(rèn)識(shí),從而交付財(cái)物,實(shí)現(xiàn)其非法占有目的。換言之,該合同的簽訂、履行行為是導(dǎo)致被害人陷入認(rèn)識(shí)錯(cuò)誤而作出財(cái)產(chǎn)處理的主要原因。利用合同即是其詐騙行為的關(guān)鍵。而對(duì)那些即使行為人也采用了合同的形式,但是被害人之所以陷入錯(cuò)誤認(rèn)識(shí)并非主要基于合同的簽訂、履行,而是合同以外的因素而使其陷入了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而交付財(cái)物的,應(yīng)認(rèn)定為詐騙罪。


本案中,三名被告人經(jīng)過合謀后,決定實(shí)施網(wǎng)絡(luò)關(guān)鍵詞詐騙活動(dòng),并且作了充分的犯罪準(zhǔn)備與分工:首先準(zhǔn)備了三張作案用的電話卡與手機(jī)卡,其次是制作了假的公司營(yíng)業(yè)執(zhí)照與公章,最后三人作了明確的分工,由吳劍擔(dān)任中介公司的角色,負(fù)責(zé)打電話聯(lián)系關(guān)鍵詞持有人,告知其有買家愿意高價(jià)購買關(guān)鍵詞;由劉凱充當(dāng)買家,與被害人簽訂收購關(guān)鍵詞合同,誘騙被害人補(bǔ)充提供關(guān)鍵詞檢測(cè)報(bào)告等完善關(guān)鍵詞的材料;張加路充當(dāng)?shù)谌焦炯夹g(shù)服務(wù)人員,幫助被害人制作所謂的檢測(cè)評(píng)估報(bào)告等材料。在這個(gè)過程中,被害人受高額收購價(jià)格的誘惑,一步步陷入被告人設(shè)置的陷阱,不斷支付完善關(guān)鍵詞的費(fèi)用。
在整個(gè)犯罪過程中,涉及兩個(gè)行為內(nèi)容,第一個(gè)行為是被告人與被害人簽訂關(guān)鍵詞收購合同,第二個(gè)行為是被告人要求被害人完善關(guān)鍵詞,并提出很多完善的項(xiàng)目,包括制作關(guān)鍵詞檢測(cè)報(bào)告、申請(qǐng)專利、注冊(cè)國(guó)際端口、制作B2B證書等,繼而被告人再冒充第三方技術(shù)服務(wù)公司的人員誘使被害人交付有關(guān)制作費(fèi)用,被害人被騙取的正是后者所謂完善關(guān)鍵詞的費(fèi)用。從收購關(guān)鍵詞合同的內(nèi)容來看,并不包括幫助被害人完善關(guān)鍵詞并收取費(fèi)用的內(nèi)容,即簽訂收購合同與誘騙完善關(guān)鍵詞是兩個(gè)相對(duì)獨(dú)立的行為,不存在包容關(guān)系。本案被告人的犯罪手法多樣,通過簽訂收購合同——誘騙完善關(guān)鍵詞——收取所謂的完善關(guān)鍵詞制作費(fèi)用,進(jìn)而達(dá)到騙取財(cái)物的目的??梢?,簽訂收購合同只是一個(gè)誘餌,被害人并非基于該收購合同交付費(fèi)用(相反,基于收購合同,應(yīng)該是被告人向被害人支付收購費(fèi)),而是基于后續(xù)的完善包裝關(guān)鍵詞的環(huán)節(jié),相應(yīng)地支付了相關(guān)費(fèi)用。因此,從整體評(píng)價(jià)的角度,被告人的多種犯罪手法互相配合,前面的行為都是犯罪過程的環(huán)節(jié)之一,最終目的就是騙取制作完善關(guān)鍵詞的費(fèi)用。換言之,被告人騙取財(cái)物的核心手段就是誘騙被害人完善關(guān)鍵詞,而這個(gè)手段并不是基于合同,因此本案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本質(zhì)特征,而是由于被告人的其他欺騙行為,使被害人產(chǎn)生“需要完善關(guān)鍵詞”的錯(cuò)誤認(rèn)識(shí)而交付財(cái)產(chǎn),故而應(yīng)認(rèn)定為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