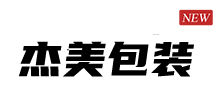深圳家暴離婚專業(yè)律師 休息幾天,我又像什么也沒有發(fā)生過一樣,通知她們來干活,我以為,也愿意相信,不會(huì)再有下一次,可是一次比一次更厲害。
2015年,一次酒醉之后,他半夜回來,開始找事,詢問是不是和他的藏族朋友(男子)有事,暴打是突然開始的,我的眼睛登時(shí)模糊了,拳頭不斷砸在我的頭上,頭發(fā)被抓著,動(dòng)不了,只聽見孩子大哭著,孩子父親喊著:“你看著你的阿媽!”頭被擊打的瞬間,我的小便失禁了。

一直打到早晨,我不知道衣服上哪里來的那么多血,手機(jī)還能看清,我沒有報(bào)警(也許這是最糊涂的,一次也沒有報(bào)警),孩子還睡著,我叫來女工周毛,只電話說,我快被打死了……她帶上丈夫一起來勸孩子父親,我?guī)е鴾喩淼膫瑫灂灪鹾醯氐搅宋鲗帲嗪H嗣襻t(yī)院,檢查是眼球血腫,眉骨骨折。醫(yī)生需要給眼珠上注射藥物,同時(shí)吃含有大量激素的藥物治療眼睛,孕婦禁服,也就是這時(shí)候,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有了老三。
醫(yī)生說,你治眼睛就不能要這個(gè)孩子了。
我說,我要孩子。
我妥協(xié)了,回家了。
僅僅不到一個(gè)月,他和一個(gè)藏族女工在一起被我撞見,我抓著他的衣服問,為什么,為什么?我被一腳踹在肚子上,開始流血了。
我?guī)е挥惺謾C(jī)和身份證,曾經(jīng)的好朋友,作家洪峰的媳婦蔣燕,聽到,只說,趕緊來。機(jī)票是她買的,飛機(jī)落地,她的農(nóng)場司機(jī)開車在機(jī)場等著,連夜把我拉到了她家。
哪里還在疼,好像也不知道了,只知道一直在流血。蔣燕是祖?zhèn)鞯囊歪t(yī),她說,你的老三怕是保不住了。你自己決定,要不要回去。
作家洪峰無論到什么年紀(jì),都是個(gè)桀驁不馴的人,蔣燕叫他“老頭”。我們上一次見面,還是十年前采訪的時(shí)候。這一次,“老頭”什么也沒有說,也沒有問,只給廚房的姑娘說,趕緊去下一碗面。
血流了兩周,青海的藏族女工們發(fā)微信問:“嫂子,你在哪兒?”
“我們一直沒有活干,等你回來。”
“嫂子,你在哪兒?你回來到我家里來,我給你做面片吃。”
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大,2011年,兩個(gè)月的他,就在翻越雪山時(shí)和我一起出了嚴(yán)重的車禍,嚴(yán)重右腦錯(cuò)裂傷,醫(yī)生幾次勸我放棄搶救,他活下來,3歲半才開始走路, 智力發(fā)育遲緩。自己在哪里,我的電話,名字,什么都說不上,總是餓,總是迷路。
我給洪峰老師和蔣燕說,我要回家,孩子和藏族女工都在等我。
血繼續(xù)流著,蔣燕說,你不要做任何事了,如果孩子留不住,就是天意,你就坐在床上不要下來,一直喝雞湯。
于是整整一個(gè)月,我坐在床上工作,雞湯是藏族女工們輪流在爐火上熬的,端給我喝,我慢慢好起來,血止住了。
可是這樣的日子,沒有結(jié)束。
幾乎每個(gè)月,都會(huì)卷土重來,有時(shí)是因?yàn)榫疲袝r(shí)是因?yàn)槟行裕热鐑?nèi)地媒體同事自駕來青海,路過家里來看看我。
我總是愿意相信,相信一切會(huì)結(jié)束,相信人會(huì)改變,相信前面的路。
窺破一切真相的縣文聯(lián)老師說,金瑜,上天給你這一雙手,是讓你寫字的。
我一直很少哭,唯有這一句,嚎啕大哭。
幾位文聯(lián)的老師都是老青海人,那一次他們抽了好多煙,說,我們這里,打倒的媳婦,揉倒的面,我們幾個(gè)男的,去管去勸,還要惹一身騷,說我們和你有事情,說不清啊……你自己要爭口氣,不要倒下,不要認(rèn)命。
你還有三個(gè)尕娃呀!
這個(gè)世界上,哪里有世外桃源呢?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名氣大了,我們的蜂場被一伙人盯上,正是采蜜的季節(jié),“蜜蜂搬走,不然現(xiàn)在就點(diǎn)掉!”他們要把一百多箱蜜蜂用汽油活活燒死。另一個(gè)荒攤上,一個(gè)村支書掂來了一桶汽油,對(duì)我們看守蜂場的工人說,兩萬,現(xiàn)在拿來!
村里人說,那個(gè)馬金瑜,坐在屋子里咋樣能掙錢呢?除了念經(jīng)的活佛和喇嘛,誰能坐在屋子里掙錢呢?我們青海的土豆也在網(wǎng)上賣著(大雪之前,我曾經(jīng)把村里積壓的土豆全都幫村民賣掉了),肯定掙得都是黑心錢。
和孩子父親一起的村民說,借五千塊,你都拿不出來,你媳婦把錢管著,你算個(gè)啥男人?把一個(gè)女人家管不下?治不服?
孩子父親的親戚給他說,這個(gè)啥電商生意,你一個(gè)男人做不了嗎?非要讓一個(gè)女人騎到頭上?你把她治不服嗎?
我可以保護(hù)蜜蜂,可以保護(hù)女工,卻不能保護(hù)孩子和我自己。半夜醉酒,翻墻進(jìn)來,從房頂上跳下來,把我叫醒開始找事打架,孩子醒來,他讓孩子在旁邊看著。
他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要網(wǎng)店的密碼。
他開始下手打得越來越重。
縣電視臺(tái)的記者同行哭了,她看著我臉上的紫色印子,那是孩子父親坐在身上用手不停扇的。
我那時(shí)還在說,不要打我的眼睛。
總想著,有眼睛,我還可以寫字,養(yǎng)活孩子。
2017年元月春節(jié),他半夜溜出去和一個(gè)藏族女大學(xué)生開了房,也是之前來這里工作的女孩。
他只說,我喝酒了。
我問女孩,如果懷孕了,你打算怎么辦?
她說,我生下來。
我又問,你是那么虔誠的一個(gè)人,你和他在一起的時(shí)候,你磕頭的綠度母,白度母,在哪里?
她說,金瑜姐,對(duì)不起,我對(duì)不起你。
我說,離婚吧,生意我也沒法支撐了,孩子的父親說,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做不了這些事,我一個(gè)人也養(yǎng)不活三個(gè)孩子。
艱難痛苦的日子里,女工和男工沒有走,還在堅(jiān)持發(fā)貨,春節(jié)前,我請(qǐng)大家吃他們都愛吃的火鍋,謝謝你們,剛剛開口,我已經(jīng)說不下去了。
我們勉強(qiáng)熬著,我不知道前路在何方,每一次挨打受氣,我出門后,女工都到黃河邊去找我,這個(gè)縣城離黃河很近,每年都有跳河尋短見的媳婦。
一直到為了安排女工的工作,家里只有我和孩子父親兩個(gè)人的時(shí)候,他說的意見,我說不行,不知道哪里來的怒火,他突然把我掐住脖子摁在床上,只在那幾秒,他的眼睛紅紅地狠狠地直視著我,他動(dòng)了殺機(jī)。
沒有呼吸,我很快什么也看不見了,眼前是黑的,也許已經(jīng)昏過去了。
等我再次睜開眼的時(shí)候,他在床邊坐著,我看不清表情,我聞到了臭味,我已經(jīng)被掐得大小便失禁了。那是一個(gè)中午,陽光還很好。孩子都被藏族阿姨秀措帶出去轉(zhuǎn)了。
2017年6月初,我的母親心梗在新疆病危,我返回新疆,湊錢救治,6月底,母親走了。她看著我,好像還有很多話沒有說。
10月底,我的二弟被神經(jīng)母細(xì)胞瘤帶走了,在昏迷中。
我是回族,母親和弟弟都是土葬,送他們的時(shí)候,很大很冷的雨水,我也很想走了。.

我半年沒有回青海,從春節(jié)開始,每個(gè)月回去看一下孩子,但還是在撐著網(wǎng)店,借錢進(jìn)貨,給還在堅(jiān)持的工人發(fā)工資,交庫房房租,交孩子學(xué)費(fèi),交順豐運(yùn)費(fèi)……2018年六一,我第一次帶著老父親和大弟回青海看孩子,從西寧回貴德的路,有一段是沒有樹木和綠草的,全都是紅色的土坡,雨水多年沖刷的痕跡溝溝坎坎,沒有一棵樹,老父親開始哭,一直流淌著眼淚,不停說一句,誰讓你嫁到這里來的……
我始終沒有能力帶走孩子,孩子的父親也多次威脅,在微信上寫:“讓我們一起死吧。”“把孩子全部吊死吧,讓我們一起死在草原上吧!”
他自己找了一個(gè)漢族保姆,保姆費(fèi),孩子撫養(yǎng)費(fèi),廉租房的電視,油煙機(jī),孩子感冒住院……所有的,都是我在承擔(dān)。終于有一次,我沒有通知他們,和朋友一起,提前到縣城看孩子,智力發(fā)育遲緩的老大,在七月炎熱的中午,穿著冬天的棉褲,衣服里面的大便已經(jīng)干透了,成了硬殼,孩子一個(gè)腳踏拉著布鞋,一只腳穿著一個(gè)大拖鞋,身上已經(jīng)很臭了,孩子手指頭疼,帶去診所的時(shí)候,孩子的手指甲輕輕掉了,指甲下面都是膿水,孩子已經(jīng)不知道疼了幾天了。老三還小,牙還沒有長起來,孩子父親找的保姆給孩子塞了一塊很硬干透的饃饃,老二的球鞋沒有鞋墊,里面就是一格一格的硬塑料鞋底。
我去找在縣城工地上做飯的藏族保姆秀措,給她看孩子掉下來的指甲,我說,你來照看孩子吧。她邊抹眼淚邊點(diǎn)頭。
秀措照看孩子不到一個(gè)月,孩子的父親喝了酒開著車滿小區(qū)滿縣城亂轉(zhuǎn),三個(gè)孩子在四樓的窗戶上趴著,孩子的父親把孩子鎖在家里。陽臺(tái)窗戶沒有柵欄,沒有紗窗,夜里已經(jīng)很冷了,秀措和丈夫擔(dān)心孩子從樓上掉下來,在樓下守了一夜,直到早晨七點(diǎn)看到孩子父親回家。
這一天早上九點(diǎn)多,等藏族阿姨秀措重新返回,老大光著腳站在小區(qū)的土路上在大哭,進(jìn)了屋子,孩子的父親還醉著躺在臥室里,5歲的老二拿著通著電源的電鉆,在墻上鉆著,3歲的老三在一片狼藉中,拿著吃肉的利刃揮來揮去……秀措哭著打電話給我,小馬,再干不成這個(gè)活,我看不了了。
我終于決心帶孩子們離開,就是淪落到要飯,也要把他們帶在身邊。
我問已經(jīng)轉(zhuǎn)行做律師的前同事,如果分居期間,母親帶走孩子,算不算違法?
許久,他回復(fù):不算。
我沒有帶任何人,只有我一個(gè)人,我知道,一旦和孩子父親搶孩子,一定會(huì)出人命。
如果我死了,也沒有關(guān)系。
如果我活著,我就把孩子帶出來。
我找了一輛出租車,只有藏族阿姨秀措和孩子在家,老三還在睡著。
秀措不知道我要來,迷迷糊糊地從孩子旁邊爬起來,問:“你回來了嗎?我給你燒茶。”
我把老三抱起來,把老大老二拉過來,我們都跪在了秀措面前,我說,給秀措阿姨磕三個(gè)頭。我也深深磕下去,抬起頭來已經(jīng)淚眼模糊,秀措也在哭,她拉我們起來,我還是跪著說,秀措,我今天要把孩子都帶走,孩子在他爸爸手里,眼看就要出事。
秀措哭著光是點(diǎn)頭。
她說,對(duì)著,這樣下去孩子要出事。
又說,你們走了,我咋辦?
我說,對(duì)不起,秀措。
秀措哭著,把她厚的衣服給我穿上,說下雨了冷得很,又把小毛毯給老三卷上,說,娃娃不要感冒了。
我沒有再回頭,把他們?nèi)齻€(gè)帶上出租車,眼淚和外面的雨水都流淌著。
我提前寫了一封長信,寫孩子父親怎么打我,和保姆一起怎么對(duì)待孩子,寫我為什么帶孩子們離開,三個(gè)孩子的小腿,腰上,這時(shí)已經(jīng)被醉酒的父親用皮帶和皮帶扣抽爛了,紫色的淤青……在路上,我把長信發(fā)給縣文聯(lián)和宣傳部的老師,委托他們交給縣婦聯(lián)和公安局。
孩子們都很好奇,媽媽,我們?nèi)ツ膬海?dòng)物園嗎?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孩子們?cè)谀膬海瑥?017年7月開始,有段時(shí)間我們總吃掛面,被不同的房東趕出來過兩次,因?yàn)樗麄兲沉耍麄冞€是那么愛笑,那么調(diào)皮。
我有許多事不能做了,或者說中斷了,原來主打的商品青海蜂蜜我很久沒有發(fā),微店管理方(北京口袋科技公司)支持的在當(dāng)?shù)啬羺^(qū)幫助留守婦女的藏雞養(yǎng)殖項(xiàng)目中斷了,牦牛藏羊肉、枸杞、黃菇……所有的供應(yīng)鏈全部都中斷了(大多是青海海南州貴德縣和周邊的貴南縣、澤庫縣、河南縣、湟中縣)。在三年的時(shí)間里,我湊錢借錢,一點(diǎn)一點(diǎn)重新尋找供應(yīng)鏈,同時(shí)面對(duì)著我和三個(gè)孩子的房租,我們的生活費(fèi),幼兒園學(xué)費(fèi),老大的特殊教育學(xué)費(fèi)(自閉癥和智力發(fā)育遲緩)……
有多艱難呢?比起和我曾經(jīng)一起工作的藏族女工,我已經(jīng)太容易太幸運(yùn),我識(shí)字,上過學(xué),雖然我沒有詳細(xì)說過為什么如此落魄,許多同事和朋友,依然默默地十分信任地幫助我,在最艱難的至暗時(shí)刻,給我最珍貴的光亮,借錢給我,找渠道給我,推薦工作給我……用他們和她們所能想到的一切辦法。
最崩潰的,來自心,來自信念的崩塌。而這一切,需要把心的一個(gè)一個(gè)碎片沾起來。我相信人,相信人性,但人性的黑暗與邪惡,始終是我始料未及的,時(shí)至今日,還有許多關(guān)于我的風(fēng)言風(fēng)語,比如我是跟人跑了,比如我是卷錢跑了——即使是曾經(jīng)生死與共的藏族女工,沒有一個(gè)女工敢站出來作證我經(jīng)歷的家暴,“我們的老人和娃娃也在這里呀,出點(diǎn)事情咋辦呢……”,是這樣的,作為一個(gè)外鄉(xiāng)人,我都理解。家庭暴力是一種違法行為。我國幾年前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現(xiàn)在各省都制定了相關(guān)實(shí)施辦法。但是,很多朋友并不太了解家庭暴力以及處理家庭暴力的措施。給大家介紹一下。
一、什么是家暴?
家庭暴力,即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通過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頻繁虐待和恐嚇等方式實(shí)施的身心侵犯。
在司法實(shí)踐中,有三種類型的家庭暴力:
1.身體暴力:一方家庭成員毆打另一方致死、致殘或重傷;家庭成員經(jīng)常拳打腳踢、掌摑等人身傷害或羞辱;婦女在懷孕和分娩期間被配偶?xì)颍槐坏谌呔砣肱渑嫉纳眢w傷害行為等。
2.精神暴力:一方家庭對(duì)另一方的冷暴力、頻繁威脅、恐嚇、侮辱,造成對(duì)方精神疾病;以傷害相威脅,破壞家具,傷害動(dòng)物,打罵孩子,威脅對(duì)方精神恐懼,威脅安全等等。很多朋友不重視這一點(diǎn)。其實(shí)長期虐待依然會(huì)構(gòu)成家庭暴力。以前有孩子長期虐待父母,導(dǎo)致父母一直處于恐懼之中,法院做出了禁止相關(guān)行為的人身保護(hù)令。
3.性暴力:經(jīng)常以暴力方式強(qiáng)行與配偶發(fā)生性關(guān)系,造成危害后果的;飲酒后強(qiáng)行與配偶發(fā)生性關(guān)系,使對(duì)方無法忍受;以暴力等方式對(duì)配偶進(jìn)行強(qiáng)迫性虐待。
所以,如果存在上述行為,可以判定為家庭暴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夫妻間偶爾的打架斗毆,如果不損害對(duì)方的人身自由和身心健康,不構(gòu)成家庭暴力。
二、面對(duì)家暴?.

1.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單位、居民委員會(huì)、村民委員會(huì)、婦聯(lián)等單位投訴、反映或者求助。有關(guān)單位接到家庭暴力的投訴、反映或者求助后,應(yīng)當(dāng)給予幫助和處理。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也可以依法向公安機(jī)關(guān)舉報(bào)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如果有經(jīng)濟(jì)困難,也可以申請(qǐng)法律援助。
2.實(shí)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遺棄家庭成員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不構(gòu)成犯罪,構(gòu)成違反治安管理的,依法處罰。
3.因家庭暴力導(dǎo)致夫妻關(guān)系破裂,受害方可以在離婚訴訟中要求加害方賠償。賠償包括物質(zhì)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
4.申請(qǐng)人身保護(hù)令。當(dāng)事人因家庭暴力或者家庭暴力的真實(shí)危險(xiǎn)向人民法院申請(qǐng)人身安全保護(hù)令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受理。當(dāng)事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因受脅迫、脅迫不能申請(qǐng)人身安全保護(hù)令的,其近親屬、公安機(jī)關(guān)、婦聯(lián)、居民委員會(huì)、村民委員會(huì)、救助管理機(jī)構(gòu)可以代為申請(qǐng)。
人身安全保護(hù)令可以包括以下措施:(一)禁止被申請(qǐng)人實(shí)施家庭暴力;(二)禁止被申請(qǐng)人騷擾、跟蹤和聯(lián)系申請(qǐng)人及其相關(guān)近親屬;(三)責(zé)令被申請(qǐng)人搬出申請(qǐng)人住所;(四)保障申請(qǐng)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被申請(qǐng)人違反人身安全保護(hù)秩序構(gòu)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zé)任;尚不構(gòu)成犯罪的,由人民法院給予訓(xùn)誡,并可根據(jù)情節(jié)輕重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15日以下拘留。
深圳家暴離婚專業(yè)律師 同時(shí),一些地方如果受到刑事處罰、治安管理處罰或者違法者違反人身安全保護(hù)令,也會(huì)在個(gè)人信用記錄中被記錄為不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