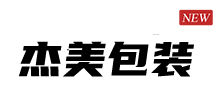深圳專業財產糾紛律師 合同詐騙罪是詐騙罪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表現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通過虛構標的物,騙取他人財物。我國刑法第224條【①】和第266條【②】規定了合同詐騙罪和普通詐騙罪。由于合同詐騙罪是一種特殊的詐騙罪,它必須符合詐騙罪的基本要件。但合同詐騙罪要求行為人利用經濟合同作為犯罪手段實施欺詐,即在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中,騙取對方財產。

近日,筆者工作的刑警隊接到類似案件,犯罪嫌疑人以還貸金融項目向被害人借款,并承諾償還本息。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先履行了部分合同。但到了后期,由于流動性被破壞,項目無法運營,犯罪嫌疑人仍在向被害人集資,直到項目徹底爆炸。
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是本案的切入點,即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合同履行過程中詐騙他人財物的故意不是非法占有的目的,則不能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犯罪嫌疑人。反之,犯罪嫌疑人可能構成合同詐騙罪。
但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釋標準是什么?而當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是在簽訂合同之前,而是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是否構成合同詐騙罪是本案的重點。筆者想結合案件的基本情況,結合當前的司法實踐,對合同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進行分析和解讀。
1.陷阱合同欺詐的識別。
根據我國刑法的明文規定,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采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詐手段,騙取對方財產,數額較大的,構成合同詐騙罪。合同詐騙罪是獨立于一般詐騙罪的一種獨立的犯罪。根據特別法優于一般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和《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本法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不應以一般詐騙罪論處。
根據《刑法》第224條的規定,陷阱型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一般可以抽象為犯罪嫌疑人履行部分合同義務,對對方當事人造成履行合同的假象,從而利用合同實施欺詐。
從社會危害性來看,合同詐騙罪屬于法定犯罪。犯罪嫌疑人一方面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權,同時也造成了市場秩序的破壞。這也是刑法第三章規定合同詐騙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原因。為此,合同詐騙罪的客體——合同應當作限制性解釋,即應當解釋為“經濟合同”。只有當經濟合同是犯罪對象時,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才能理解為破壞市場秩序。另一方面,合同詐騙罪屬于結果犯和數額犯。合同詐騙罪畢竟屬于合同領域的詐騙罪的表現。因此,合同詐騙罪只有在犯罪嫌疑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實施欺詐,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的情況下,才能構成。【③】也從側面反映了無犯罪結果的合同詐騙不受刑法規制。[④]
主觀上,合同詐騙罪屬于故意犯罪的范疇。根據《刑法》第十五條,犯罪嫌疑人只有在刑法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才能受到處罰。然而,《刑法》第224條沒有規定合同欺詐或法律擬制。因此,基本可以認定合同詐騙罪的主觀心理狀態只能是故意。再者,只要犯罪嫌疑人捏造事實,隱瞞真相,就不是合同詐騙罪。犯罪嫌疑人被評價為合同詐騙的,主觀上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換句話說,合同詐騙罪要求犯罪嫌疑人有直接故意,并積極利用合同促成詐騙。
合同詐騙罪的成立雖然強調了“非法占有目的”的構成要件,但非法占有目的畢竟是主觀的。關于主觀狀態的判斷,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通過司法推定的證明規則推定犯罪嫌疑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比如利用陷阱進行合同詐騙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明知涉案項目資金已經破碎無法操作,仍然向合同當事人集資,根據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可以直接推定犯罪嫌疑人有非法占有目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合同詐騙罪的判斷取決于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時是否利用了合同實施的欺詐,該行為是否危害市場經濟秩序,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釋。
如上所述,合同詐騙罪要求犯罪嫌疑人在犯罪過程中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在審查判斷非法占有目的時一般會采用司法推定的證明規則(當然是犯罪嫌疑人提出相反的證據進行推翻或反駁)。即合同當事人是否具有完善的履行合同的權力,從而判斷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但合同詐騙畢竟不同于誣告、強奸等犯罪行為(行為與結果同時發生或間隔很短),尤其是陷阱型合同詐騙。行為和結果之間的間隔一般更長。而且判斷合同雙方能否令人滿意地履行合同也不是時間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很可能出現資金鏈斷裂或其他情況,導致合同無法履行。或者,犯罪嫌疑人雖然在簽訂合同時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隨著資金的注入,公司或項目起死回生,犯罪嫌疑人放棄了騙取財物的想法。因此,當事人是否有能力履行合同,或者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是否有能力履行合同,在邏輯上不能達到自洽。因此,與其用履行能力來判斷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如用其他標準來解讀非法占有的目的。
履約能力不能一成不變,也沒有具體的量化標準。如果采用固定的量化標準進行形式判斷,必然會影響司法判斷的準確性,尤其是涉及資金較大、合同履行期較長的合同。因此,與其以當事人履行合同的能力來判斷當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如以當事人對標的物的處分來分析當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在合同案件中,必須涉及當事人對標的物的處分,這為判斷解釋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提供了依據。而且,標的物本身的處置情況可以直接客觀地反映犯罪嫌疑人對合同的態度。比如,在筆者所在團隊收到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履行后來的合同義務時,屬于違反合同義務,非法占有合同相對人財產的目的也是“明顯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第三條的規定,通過處分標的物判斷非法占有的目的已逐漸被司法機關所接受和認可。
至于非法占有目的產生的時間點,應該解釋為合同簽訂之前還是之后?筆者認為合同詐騙是一個動態的犯罪過程。因此,即使非法占有目的是在合同履行中產生的,也應解釋為構成合同詐騙罪,但非法占有目的形成前的數額可以排除在本罪之外。
第三,案例分析。

法院在審查合同詐騙罪時,一般更注重人民法院主要審查發票、收據、銀行流水、公司會計賬簿等證據來證明小額履行或部分履行的證據,通過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銀行賬戶、債權債務關系、資產調查、公司審計報告等來判斷被告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口頭證據方面,人民法院審查的證據包括:1.被告的供述和辯護。重點考察被告人在供述中是否承認自己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被告辯稱自己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重點考察其供述中描述的合同簽訂和履行過程,包括合同簽訂前的準備、履行能力、貨源、合同簽訂后對合同標的物的處置、被告違約后是否采取了補救措施、違約的態度等。2.受害者的陳述。分析被害人的陳述與被告人在上述重點檢查中的供述是否一致。3.證人的證詞。在合同詐騙罪中,證人證言主要存在于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家屬或者受雇人員中,也是為了驗證和補強上述證據。
深圳專業財產糾紛律師 客觀證據與口頭證據相結合,對于合同詐騙罪,即使犯罪嫌疑人在合同履行的初始階段履行了部分合同。但后期,資金到位后,受害者被殺。